版面导航
城隍司法文化的多元解读∶乾隆朝浙江亏空贪腐案探微
沈玮玮,万仁岢
□ 沈玮玮 万仁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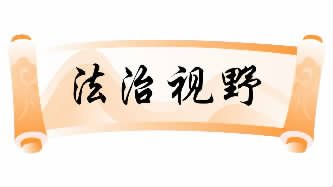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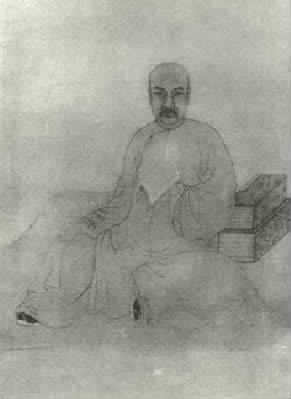
《清代学者像传》之《窦光鼐像》。资料图片
清乾隆五十一年(1786年),浙江省平阳县举子将本县县令黄梅挪用勒捐并贪污腐败之事通过考卷披露给了当时的浙江学政窦光鼐,他欲上折揭发黄梅贪腐。但考虑到学政身份和职责所在,他便将其案与整个浙江府库亏空之象捆绑呈奏,于是将江浙之财政和官场现状和盘托出,拉开了当时号称浙江三大贪污案之首的“黄梅案”的序幕。
乾隆帝在得知此事后,曾下派两拨钦差奔赴浙江查案。钦差揣度圣意,同时为了权衡其利益,不断攻击举报人窦光鼐,最终迫使皇帝相信学政乃夸大其词并对其严厉惩治。窦光鼐拒不接受此结论,径自赴平阳以证清白。所幸的是,凭一己之力,窦光鼐最终获得了大量来自当地士绅和民众的口供和物证,可谓证据确凿,所揭发的平阳县令和浙江官场亏空之事并非“误听人言”“风闻入奏”,让钦差和浙江官场的集体谎言不攻自破。
取证地点之别
窦光鼐身为学政,既无行政之权,更无司法之责,能成功“挑战”整个浙江官场和朝廷钦差,皆因他获取了铁证。只不过拿到这些证据并非易事,窦是通过更换取证地点至城隍庙才得以如愿的。就此而言,城隍庙才是浙江亏空贪腐案被成功揭发的关键。然而,或许是因为窦光鼐在禀奏时刻意回避其城隍庙取证之过程,以往研究城隍信仰及其司法功能的成果才并未关注到此案。窦之所以故意隐瞒取证场所,意在否认身为一省思想领袖之学政,断不可利用怪力乱神或神道设教之偏门取证的做法,否则便有损其物证和人证之证明力。后世在利用城隍取证侦破疑案之时也多有此顾虑,看来回避或否认利用城隍侦讯或许是一种惯例。
因先后两次的取证地点不同,取证的对象即当地的生员出现了两种截然不同的反应。在明伦堂取证时,生员“皆答云不知”,致使窦光鼐“发怒咆哮”;而在城隍庙取证时,生童民人却“拥至千百成群、纷纷嘈杂不堪”。为何有如此大的差别?众所周知,江浙历来为赋税重地,其富裕程度不言而喻,乾隆帝断然不会相信江浙地方财政能出问题。在此前提下,浙江官场可谓“铁板一块”,对亏空之事守口如瓶。作为外放地方的学政,窦光鼐在临行前曾得到皇帝的口谕,可以将所见所闻如实奏报,尽管学政并不干预或无权干预地方(包括司法)。考虑到窦光鼐此前的为官履历和司法经历,皇帝的提醒意在表明,当时中央无法通过正常的公文传递渠道甚至监察体系了解到地方“真相”。甚至连明伦堂这种看似不太官方的场所,早已被士人视为正规的府衙,与其他官府无异。更何况窦学政还兼领吏部侍郎之衔,乃堂堂正二品大员,士子更是难以彻底放下芥蒂呈递证据,窦光鼐难以在明伦堂取证便容易理解。
明伦堂代表的是官方正统的司法(治理)场域。城隍庙则不同,其代表的是民间大众信赖的司法(治理)空间,向民众普遍开放,可随时进出,自然自由不少。因此,窦光鼐移至城隍庙后,铁证便蜂拥而至。如此表明,至少在乾隆朝晚期,城隍神所营造的官民信息沟通渠道已成为廉吏采风获取民意的不二之选,乾隆《嘉定县志》《孝义县志》等江浙地方档案随处可见城隍庙之记载。更重要的是,据《乾隆御制初建城隍庙拈香礼八韵有序碑》载,在京郊热河城隍庙落成之时,乾隆帝更是亲自拈香瞻礼以示其礼重。以往研究城隍司法之成果所引案例多在清代晚期,窦光鼐此举或印证了早在清代中期,城隍庙已经成为官府获取包括司法线索在内的有关地方政事和基层民意的关键言路。
取证主体之殊
已有的研究之所以忽略此案,还在于取证主体并非司法主官。窦光鼐之身份乃一省学政,因此,乾隆帝既可以像钦差大臣伊龄阿等人认为的那样,窦是“罔顾君命一意孤行”,并且“擅离职守延误本职”,算得上是越权取证;又可以认为窦并非行政主体,而是该案的当事人。就此而言,作为该案的当事人试图通过取证自证清白,并非“一意孤行”和“擅离职守”,倒是为了辩冤的“自力救济”。上至中央两番钦差调查团,下至浙江全体官僚同仁,都无法让窦光鼐冤屈能伸,只能证明乾隆晚期吏治已经腐败透顶,既有的司法公正保障机制已经失效。窦光鼐只能依赖于不可言说的神道设教来尝试获取有力的证据,而不论他是否真的信仰城隍神。
是否真如钦差在奏折中所言,窦之所以能够获取证据,是通过“用刑恐吓”“怂恿士子”“挟制官长武断乡里”等非法手段?这些手段同样可以在明伦堂采用,为何又没有奏效?对于受过儒家熏陶的士子而言,“以德报德”才是他们正确的处事态度。既然窦光鼐不顾自己的官帽和人身安危,以身涉险,大胆揭发平阳县令黄梅贪腐和整个浙江府库严重亏空之事,士子便认可了窦的清正和公道;再加上先后历经两次钦差调查,后又经皇帝亲自定夺,窦光鼐依然不服,且主动在明伦堂取证之姿态,足以证明窦光鼐是真正站在士子草民这一边的。那为何在明伦堂窦的取证并不奏效,反倒是在城隍庙就可以如愿以偿?这其实体现出了浙江平阳士绅的家国情怀。北宋大儒张载著名的“横渠四句”在此被平阳的士绅践行得十分彻底,即城隍庙的成功取证可以被视为平阳士绅和百姓共同心声之体现。明伦堂呈证只能代表士绅阶层的态度,并不能真实地反映底层民意。更何况窦为学政,乃士绅领袖,在旁人甚至皇帝看来,窦在士绅群体中具有相当大的影响力。倘若取证成功,他就会被视为以权谋私,证据的可靠性会大打折扣。士绅为了保护学政,自然不敢畅所欲言。窦光鼐要拿到铁证,必须要“排除合理怀疑”。即便窦在最后出示铁证时对城隍庙之事尽可能闭口不谈,但其获取到了从官员“捐职布政司理问吴荣烈”,到“监生邱云彩”“生员陈传人”“生员陈廷瑞”等,再到“老民缪元章”等无比多元丰富的证据,便会打消皇帝或臣僚的疑虑。而且,窦所得到的铁证并未使用城隍信仰这种方式,只是改变了取证地点。
总之,此案所揭示的地方城隍司法之功能,绕开了已有研究陷入官方或民众是否真正信仰城隍神的“执念”,倒是揭示了城隍司法的另一种功能,即成为士绅和民众能否形成司法或治理共识的试金石。“为生民立命”是包括窦在内的所有读书人的共同愿望,士绅民众借助城隍庙这一公共空间助力窦光鼐,将读书人与浙江平阳的百姓命运紧密连接在一起,更将儒家所宣扬的士大夫之使命演绎得堪称完美。正是因此案所涉取证主体和取证过程与其他侦讯或审判具有较大的差异性,才造就了其独特性和典型性,让城隍之于地方司法有了多元化的功能呈现,值得进一步地探究。
取证效果之异
窦光鼐于城隍庙取证的过程被钦差的奏本描写得异常精彩:“(窦光鼐)以伸冤理枉为辞,以致生童民人竟拥至千百成群、纷纷嘈杂不堪,弹压等情。是处平阳地广山海、俗本刁顽,窦光鼐身为大臣,与生监等聚坐谈心,诱令……”对此,可以有其他解读:尽管窦作为当事人,但在士绅百姓眼中,他还是正儿八经的朝廷官员,所以他以伸冤理枉为辞有着双重意义:既有为平阳百姓伸冤之意,又有为自己鸣不平之虑。能够与生监(即生员与监生——编者注)百姓聚坐谈心,更是证明了他已得到生监的认可。百姓蜂拥而至,说明他的冤情已然在浙江平阳广为人知,且百姓愿意与之共进退。因此,移至城隍庙取证,很难说是他自己的想法,倒不如说是平阳民意使然。平阳生民皆受县令黄梅多年来盘剥之苦,但一直隐忍不发,好不容易有了窦的仗义执言,为民发声请命,让百姓畅所欲言,这样的机会怎能放过?民众能够目睹廉吏之风采,何其幸哉!“与生监等聚坐谈心”表明,他们一旦看到窦不顾安危抗争贪腐的决心,何须“诱令”呈送证据?百姓自然是倾其所有加以支持,主动呈上两千多份供词和物证,证据之多之丰富更是城隍庙史上前所未有的,已然超出了窦的预想。
进言之,此案所揭示的城隍司法之功能,早已超越了官员主动通过城隍信仰收集证据侦破疑难案件的认知,成为百姓主动提交证据,为清除危害一方的官蠹和支持体恤百姓廉吏的鲜活例证,具有示范效应,无怪乎钦差们在奏折中批评窦此举乃“事关地方人心风化”以恐事后效仿之。因此,城隍庙已然成为地方人心风化的观测点,民众可以借此城隍之“风化”来表达地方之“人心”所向。“事后效仿”意味着官方唯恐城隍庙会取代朝廷衙门,成为民众聚集宣泄不满,公开表达民心向背的集散地。此案或可称为城隍庙由仅承载民间信仰的“非正式机构”向官方“正式机构”转变的契机。
城隍神自唐代开始逐渐被塑造为惩恶扬善、公正司法的象征,待至清代,上至帝王,下至百姓,都对城隍信仰万般笃信,城隍司法乃至神明审判成为弥补已有司法系统不足的主要方式。已有的研究无不通过此判断强化对传统司法审判的神性认知。然而,此案表明,至少到乾隆朝后期,城隍司法功能断然不能仅局限于官府和官员的主动发挥,还被扩展为士绅百姓主动请诉的场所,乾隆帝正是看到了窦通过城隍庙获取的证据,才处理了浙江官场的亏空和贪腐。因此,此案所昭示的城隍之于地方司法乃至治理的功能,具有双重效果:城隍既可以被官方主动利用,作为取证破案之司法场域;又可以被百姓主动利用,作为上达民意之治理场域,这亦是以往研究城隍司法文化时未曾关注到的。
(作者单位:广州商学院法学院;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















